在天地之间彰显江源之美——评马文秀诗集《三江源记》

(一)青海大地时光之镜
诗集《三江源记》显示了一位少数民族诗人对长江、黄河和澜沧江这三条发源于诗人家乡的青海省南部三江源地区的,被誉为“中华水塔”的所在地河流,深情的礼赞和自然崇拜。
三江源地区不仅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而且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许多珍稀野生动物,如藏羚羊、雪豹等。三江源地区对于维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整个诗集按所写内容分为《走向高地》《灵性之光》《高原守望者》三辑,共计139首。
马文秀从《雪域回声》《老街口》《照进彼此》再到《三江源》,一路走来,正向从高原走出的一条河流,在大江大海里交汇,在北京这样一座特大的都市打拼,她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她深邃的哲理性思考,她在漂泊中神性语言、丰沛的文化自信,都显示了其卓尔不群的民族气质。
“天地万物互相供奉/于是诞生了诸多自然神话/听神话长大的孩子/在丰腴的花朵中探索高原生态之路。”(《天地万物互相供奉》)三江源之美,就是它的生态之美。万物都是有灵性的,自然也充满着灵性和神性。诗人用行走的足音丈量着那块有神迹的土地。“唐朝的岩画/留在通天河的波涛/无数探秘者穿过澜沧江流域/只为一睹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进藏的盛况。”(《崖石上的史书》)在这行走的地理中,是对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深度探秘。
“仰望星空,叫不出名字的色彩/藏在阳光之下/静听遥远的召唤。”(《替星空辩解》)
从民族的特色回溯,再回过头看第一辑《雪域回声》中的短章,我们就不难理解《三江源记》是一部向自然致敬之书,向民族致敬之诗篇。
“你我之间的那道裂缝/或许会让空白/在自然中拥有更多延伸意义。”(《荒野与我》)
“低矮的草,坚硬、青绿/紧挨着戈壁的土墙生长/此刻我需要在一首诗中对草木有所表示。”(《遗落的土墙》)
北宋画家郭熙《山水训》有记:“真山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春英、夏荫、秋色、冬骨,这是从一个画家的视角,借用森林生长的不同特点来描写四季山林景色,是一种源于中国审美精神的特有的艺术形态,正可谓“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
而诗人马文秀感受到了《万山之宗的野性美》:“三江源的广柔与粗狂/拔地而起/隐藏在万物之中/浓缩之宗,众水之源的生态秘密。”这生态秘密又是什么呢?
“艺术确确实实地潜伏在自然里,谁能把它从中剥离岀来,谁就占有了它。”(里尔克:《艺术家画像》)“诗歌创造形象。这形象始于愉悦,终于智慧。”(弗洛斯特语)
只有“在树林中间,我们回到理性和信仰。”(爱默生语)
《在玛沁收集乌云》《复盘快乐》《烟雾》《寻找打开困局的钥匙》《不可言说的相遇》等等都表现了诗人有一颗坚硬的内心,她始终在与内心较量、与时间较量、始终在与日月相争,与命运相争,她们的目光中储藏着火焰、储藏着一束光。“泪水在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哗的巨响。”(马文秀:《不可言说的相遇》)他们这些奔赴山河的诗人,梦里都有翅膀,埋着一条可以延长的河流,它能寻找机会打开时光之镜。
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要“低头,向内心祈祷;抬起头,勇敢翻越五道梁。”(《风马旗》)这也可以当作马文秀的“诗学宣言”和“生活宣言”。
(二)青海大地的淳朴柔情
《三江源记》是一部关于自然主义诗学与民族题材的诗意表达。生活和成长在青海的诗人,似乎他们的“代际传承”从来就没有断裂过。这就是以致敬昌耀为精神母题的,对于马文秀也丝毫不例外。所以,青海这块土地是有着柔情和悲悯记忆的土地。“生命的昭示,不受限于环境/青藏高原的风带着峭壁的粗狂/穿过他的身体/寄给失意的昌耀一条路。”(《生命的昭示一一写给昌耀》)
昌耀成为西部诗人一个共同的精神标识和象征。马文秀说:“我对真善美与爱的追逐,对诗意精神世界的向往,呈现在作品中是生命本色。
我在不断游历中挖掘诗意生活,诚挚记录诗意生活。我相信人世间你的热爱也换回你需要的爱,包括你的文字。行走的地域,拓宽了我的视野,新鲜的词汇涌入我的大脑,丰富了我的诗句。不同地域的人文与地理成了唤醒我内在创作的驱动力,途中所有的遇见成为我文学创作的富矿。”(《诗刊》头条诗人,2023年12月《万物皆是路标》)
“这里是远古大地地壳运动献给/青海大地的柔情/敬山敬水,敬仰世间万物/一个人总会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寻到曾经的自己。”(《青海大地的柔情》)
人不仅仅要感受到时光的柔和部分,更要感受到人性中那些善良柔软的悲悯的部分。马文秀的诗学的纹路一条是自然的生态主义,另一条就是杜甫式的现实主义,她总是饱蘸着深情去歌唱,去赞美高原生活中一个个普通的生命和灵魂。从普通人的身上去发现诗意和生活的光。
“身着藏装,坐在碉房/手抵在眉边/早已将红尘视为道场”(《百岁老妇》)
“咸而又咸的湖水/将数代盐工的故事/安放在一座座盐雕中。”(《风奏响夜曲》)
“雪山绵延起伏,生灵共处/巡山的道路不再孤单。”(《巡山》)
“随着蓝升腾/这是天空写给三江源的情书。”(《转山》)
“挖虫草的男女老少/匍匐在阿尼玛卿山腰上/为了生存他们成为自己的一面旗帜/在高海拔地区,幸福是望得见的背影。”(《匍匐在阿尼玛卿山腰上》)
诗人在游历中,执著于“对源头的探寻”,执着于对普通人和所有生命的关注,镜头和望远镜总是聚焦在一种微小、平凡和谦卑的生命和事物之间,彰显了诗人对众生悲悯的精神姿态。她常返身和深入到她的故乡青海,置身于那里的雪山、草原、冰川、湖泊与村落,注目于那里的飞鸟、星辰与光芒;她正是从青海,从三江源头,她领略着“生命的壮阔、静默、博大”。她早已经把滚滚滚红尘的一切作为她人生修行的功课,也作为了他人生修行的道场,从对源头的不懈探寻中和挖潜中,不断地获得语言和诗的灵感,让自我的灵魂不断地愈益丰富、愈益深厚与开阔。
(三)青海大地的壮阔之美
三江源这个地理性区域是有着大美的,它不仅有着生态之美、地理之美,更有着人文之美。马文秀出生在青藏高原,因此,她能以三江源揭示万物之灵的真谛,使三江源的思想禀赋在诗的世界里,把本心、本真的睿智以及对未来的祈愿,真正连在一起了。(吉狄马加语)马文秀诗学的第三条纹路就是其思辨性。在第二辑《灵性之光》、第三辑《高原守望者》中,这种思辨性得到确立和凸现。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说:“诗中之博依繁喻,乃如四面围攻,八音交响,群轻折轴,累土为山,积渐而高,力久而入。”
哲学家认为通过思辨,人可以为自然立法,也就是为自然界建立规则。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外篇.知北游》)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诗人这种对精神世界的深度关照就有了思辨色彩和哲学意味。
“荒原之上,一群狼奔跑,欢呼有谁能知晓/无数藏羚羊的哀鸣。”(《狼》
诗人的这种思考是建立在一种“对应”“对立”“天敌”(狼与藏羚羊)这种大生态关系、大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动物与动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之上的,真相是非常残酷残忍的。“弱肉强食”既是大自然的生存发展,也昭示着人类祈求着永远和平与大自然和全宇宙和谐共生的愿境。
自然,既是福地,也是竞技场,这是万物无法逃遁的宿命。
“数月后,草原上岩羊的头骨/被虔诚的信徒带回家/挂在墙上/成为了精神的图腾。”(《岩羊》)“跟人一样,没有一只藏羚羊/疲于奔命而不倒下。”(《藏羚羊的疑问》)“日落时分,一只雪豹立于峰顶/望向山岩交错的方向/目视荒芜的四野/正如他孤傲地站立在三江源”(《雪豹》)在高原民族生活中的人是需要精神信仰的,是需要神的护佑和加持的。那虚拟中或意象的神可能就是一条洁白的哈达,一具岩羊的头骨,一只雪豹在雪域高原中孤傲的身影。
《藏原羚》《青藏高原的飞》《白唇鹿》《鹰笛》等这些短诗中,人与大自然的搏弈,狩猎者对动物的杀戮,都是人类需要警醒和反省的。
在高原上万物生存之智慧,不在头顶,而是在脚下的每一次奔跑。诗人借动物世界生存的境遇,也暗示了人类命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许,正是那支鹰笛之声,越过了耸立的山峰,飞往了云端,给予人类带来了祈福、带来了和平、安宁和吉祥。
诗人依然很年轻,就像青藏高原的一阵年轻而古老的风一样,谜将解未解,随着岁月的沉淀,有些事只能在流云中去想象去填补,但也昭示着她的无限可能性和美好的未来。
2025年03月31日 发表在《文艺报 》
- 上一篇:吕进:论“新来者”
- 下一篇: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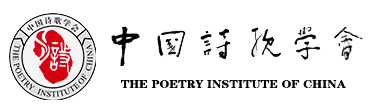


 公网安备
公网安备